晚清史学者谭伯牛与西西弗书店创始人薛野秋季在寻麓书馆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对谈。薛野现场「解」牛 、观众提问、谭伯牛分享自己的见解,由此构成了这场回应当下的,对于人生、历史的思考。
以下就是对本次对谈的回顾。

谭伯牛
晚清史学者,尤致力于天平天国史、湘军史及曾国藩传记研究。著有《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天下残局:断章取义晚清史》《湘军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盛世偏多文字狱》《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毕竟战功谁第一》《牛史 · 晚清篇》等。录有电视讲座《湘军传奇》。纪录片《湘军东征录》《近人曾国藩》学术顾问。《天国之秋》审校。

薛野
西西弗书店创始人,创新教育实践者。
现场「解」牛
薛野 × 谭伯牛
对史学的兴趣
起源龚自珍
薛野:我们先从伯牛兄开始,你是怎么产生了对史学的兴趣的?
谭伯牛:我个人对历史感兴趣可能要到初中的时候。首先是喜欢。有一个人叫龚自珍,特别喜欢他,喜欢他就想去了解。跟追星一样,你想了解他的一切。但是他是一个清代的人,你要了解这一切,你就得对他的历史背景要有了解,而一旦对历史背景要有了解,你就要学习这些知识。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是要做研究,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喜欢他的诗,喜欢他的文章。在对他背景进行了解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清代挺有意思。所以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我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
(后来)基本上就一直这么看书,又到北京做电子商务的工作。那个时候已经快30岁了,也不认识学术界的人,只知道自己天天看这种书。看了以后也没什么用。最大的用处就是非典期间在北京碰到了一个来自乐山的朋友——莫之许。
因为不懂,想去了解,才去写书
谭伯牛: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朋友,大家今天到你家吃,过几天到我家吃饭。朋友都是很熟悉的人,也不能光吃饭,聊天也没有什么别的话题可聊。他们就说,你干脆讲讲湘军的故事。三、四个人,我讲一段,他们随时可以提问。
讲了有那么两三次,老莫就讲,你不要讲了,你讲久了把真气就泻掉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我正好做出版。我说你要搞清楚,出版还是要花一点成本,万一这种东西没人看,亏本了也不太好。他说没关系,我们先测试一下。我就到了当时天涯新设的一个历史论坛,叫"煮酒论史"。
那个时候,我就每天写五千字,就写在那个论坛里面。以前的论坛好像没有点赞,只有评论。如果总是有人评论你这个帖子,你那个帖子就不断顶在上面,就可以在首页看到。我每天写五千字,一个是自己每天更新一次,一个是每天下面都有很多评论,所以早期就基本上一直在首页,也坚定了老莫出版的一个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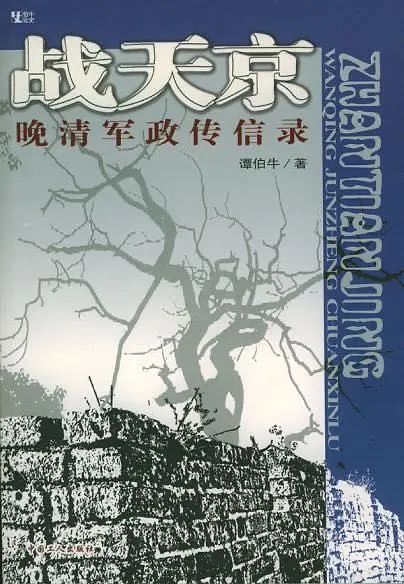
谭老师在天涯论坛上连载的《战天京》
大概花了五十天,我就在论坛上写完了这本书。写完这本书之后就发现反响还可以,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后来还有一些周刊,他们就约我写专栏。一下我就转型成为了一个文化界人士,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你研究历史什么的。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是)历史学家,(我)作为学者也有很多缺陷,所以还是认为自己是历史爱好者,就是这么过来的。
薛野:我听下来有很关键的几点,第一要有兴趣,因为一个兴趣打开就是打开了一个世界。第二个关键是,还得有一个好朋友推一把。
谭伯牛:对,要鼓励。因为他不让我去写出来的话,可能我到现在也只是知道这些知识。而且我写了之后才发现,像刚才薛野兄说你去看《湘军崛起》,你是因为不懂所以才发问。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不懂要发问,我们因为不懂,想去了解,我们才去写书。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题目,我现在(用它来)写一篇文章,我都不是完全了解,我就愿意写,因为写的过程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薛野:这个是很高明的做法,写一本书来回答自己一个问题,非常高明。
研究史学的方法
其实世间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要实事求是
薛野:你现在已经是史学的老战士了,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历史爱好者,甚至未来想做历史爱好者的人,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谭伯牛: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其实我是放弃了高考。在那个时代,学术论杂志上出现的很多论文质量是很差的。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各行各业里面的年轻人、一流的人才,大部分去经商了,另外一部分做官去了。毕业了之后真正愿意留在大学里面的,其实是那个班上成绩最差、最蠢的那一批人,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潮流。
当然现在的大学史学研究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古代史。
现在如果要提建议,我觉得当然还是应该去好学校的历史系,找到自己满意的专业去学习。
我(原来)自己在家闭门造车,有人会说你这个是民科。我说没有问题,我确实是民科,民间科学家。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八九十年代,很多人虽然在大学,在研究院里面,他本质上也是一个民科,我们要分清这一点。
我虽然是民科,但是你(如何)做考证、建立分析的框架、时刻追踪你研究问题的最新学界进展,包括一些新材料的发现、如何去辨别、去解读那些材料。这些方法虽然是我自己摸索的、自学的,其实跟学院的方法也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世间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要实事求是,最好还能清楚、明白、简要的把它说出来。
薛野:你刚才说其实不分学院内和学院外,史学只有一个,就是实事求是的史学。我很好奇你有没有内心真正拜的老师,他的史学观影响到了你。
谭伯牛:我最崇敬的史学家当然他是民国时代的張荫麟先生。張荫麟他也是一个英年早逝的学者,当时“南张北钱”,大家认为学术界最有希望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钱钟书,一个就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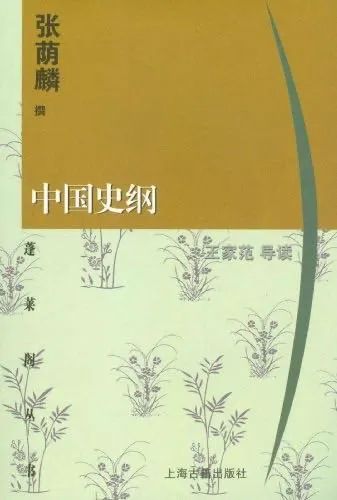
《中国史纲》張蔭麟著
大家如果有兴趣,看看他写的《中国史纲》,东汉以前的那个部分,当然那也就是他的遗著。他本来是要写一部中国史作为教科书,但是他没有写完。就那么一本小册子,那就是我最欣赏的历史的写作。经过他认真的研究之后,他可以组织一些准确的材料,然后用优雅的、优美的写作把它表达出来。
写作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认为可能一个人写作能力差,不仅仅是他文笔不好,而是他研究的水平比较低。叔本华讲过,世界上不存在说我有一个很清晰的思想,但是我文笔不足以表达,没有这回事。你说不清楚不是因为你口才有问题,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
对历史爱好者的建议
在历史中寻求美
薛野:我想把我刚才的问题再细分一下,你从当年对龚自珍的兴趣,到今天成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历史爱好者,其实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我想你给的建议(可以)分两种,一种是青年人,就是那些将来还要去求学问的人,如果他们对史学有兴趣,给他们什么建议?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今年是甲子年,大家说天下大变、世界大变。我们需要一个历史感,越大变越需要一个历史感,那么对这些想有历史感的人,你给什么一个建议?
谭伯牛:说实在的,我一般都是浇冷水。因为我认为喜欢历史的大部分都跟我一样,很多都是中年,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历史?是因为我们感觉很迷茫。越活到中年,越觉得很迷茫,不知道我所处的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个人想寻找答案,也想为民族和国家操一操心。但是说实在的,未来是完全无法预测的。
我们人往往就选择去以史为鉴,觉得历史上有什么教训,我们可以汲取一下,历史上有什么,甚至说得更直白一点,有什么套路,有什么招,可以让我更成功一点。我个人认为这是完全无效的。
第一点,因为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个事情和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局面,不管表面上看上去多么的类似,其实它都有本质的不同。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时候我也会有企业家那种培训,给他们上上课。他们也总来问,他说,我是这个公司老总,我是不是要多学点曾国藩。我说,表面上你可以调动一切,你拥有人事权、财务权,跟他也差不多。但是还有一点,他能够生死人,能够杀人,你不行,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区别,所以他的那些招你用不了。因为我的威慑力只是最多限于开除你,你对我的敬畏,跟我能一刀砍死你可不一样。所以你不要去比较,你明明没有暴力的一个许可证,你又想用曾大帅对付人的方法对付人,怎么可能呢?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没有用。

曾国藩像
还有一点,我个人比较强烈地认识到了,我们中国的历史从秦开始一直到清代,农民使用的工具几乎没有变过。虽然经过了那么多朝代,经过了那么多的变化,出现了那么多有趣或者悲剧的故事,我们觉得应该要记住很多历史上的事情,可是从秦到清并没有真正出现本质上的变化,它无非是2000年的过程。一个什么过程?就是君主专制不断得到加强,到最终进入巅峰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帝王史。
但严格说它有没有什么意义,那是一个人民不断坐稳了奴隶地位的过程。因为帝王的宝座很坚固,人民的地位就很惨痛,这个是双向的过程。人类历史上6000年,从埃及的开始,也没有太巨大的变化,直到所有人类的历史真正的变化——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前后我觉得是一个真正的关键,万古如长夜,没有工业革命的话没有光明。因为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的旗帜,它还伴随着不管它是否影响政治和经济的文化的变化,至少他们几乎是同时发生了巨变,一直到今天这个过程好像还在延续。
所以从对历史的态度来讲,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在里面学习什么成功,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可学的,关键是你在历史中寻求美。不要在历史中寻求真,在历史中寻求美,我觉得这个是最快乐的事情。
曾国藩会如何看待这个时代?
薛野:假设曾国藩穿越到今天,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个时代?他会做什么选择?
谭伯牛:这个问题以前许知远兄弟(也)问我,他当时问的是梁启超会如何看待我们的时代。我其实有一个感受,梁启超、曾国藩的困惑跟我们的困惑和感受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以前曾国藩、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他们在思考的那些问题,到今天没有解决。我们现在说的很多话是100多年前那些人早就说过的,甚至在有些问题的探讨上,人家的深度、敏感程度,比我们今天所能讲的尺度更大。
你比如说,我们讲男女解放问题,显然民国初年的女性解放运动,包括女性主义的言论就比今天要开放的多。我感觉今天年轻人里面强调三贞九烈的越来越多。当然有从一而终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对的,但是你这一点比曾国藩那个时代的人还保守了。晚清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可贵的,而不是束缚才是可贵的,那个时候人家都已经理解这个东西了。
经济上,以前的经济就已经开始有官商勾结,也存在有民族企业的出现,也有外资。尤其是从1927到1937年,所谓黄金十年之说,商业、教育、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各种各样的机缘,中间又突然给你停顿倒退几十年,好不容易又重新搞,三四十年又搞回去,这一百多年就这么折腾。
所以如果你给梁启超看一眼简报,让他看下简单的过程,他会觉得他没有什么想说,可能还得继续,就像我们现在该干嘛还得干嘛。梁启超他不会困惑,他也不会羡慕,我觉得曾国藩也差不多。
现场「解」牛 · 观众提问
Q1:如果不能以史为鉴,那么除了开心之外,你学历史还有什么用处?
谭伯牛:你都能够开心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人生最难的就是开心啊。
Q2:如果把当下比做晚清的话,哪些人是你感兴趣,也愿意去研究的?
谭伯牛:首先我不敢把今天比作晚清,大国崛起的时代应该是汉唐。这个问题是陷阱。
我个人有一个感受,我刚才特别强调的就是,研究或者阅读历史的经验不足以让你分析今天的各种事情,显然,如果那些东西有用的话,那我什么事情做不成对不对?那不可能的。我们还是继续读书而已,但是我朦朦胧胧有一种感受,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里面四川会很重要,不管是哪个方面。不是因为我在川言川,我来到这个地方。
原因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认为人有三个品德最重要,它是递进的——诚实、正直、勇敢。所以我在交友过程中我就发现在这方面,不是说别的省市没有,但是四川的朋友会多一点。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里面四川的朋友有这么一些特质的话,未来这个国家如果有很大的变化,四川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Q3:胜利者书写历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请问如何去了解真实客观的历史?
谭伯牛:胜利者书写历史,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哪怕是希特勒这样的人,他写的历史里面也不会告诉你,做种族清洗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没,有比这些更高的一些价值,谁都不敢违背。所以胜利者书写的不重要,你只是要注意到谁写的,尤其是有力量的人写的,他那个结论你要有点怀疑。写历史的一般都活着,活着就是胜利,一般就是成王败寇,历史上的事情也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不必太在意,只是你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就可以了。
Q4:如果历史是那么被后人决定的话,我们人的意义在哪里?
谭伯牛: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去寻找的地方。如果历史的过程是人类不断从黑暗走向光明,跃过重重险阻,取得最终胜利的那么一个过程的话,那我们的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垫脚石、做好螺丝钉、不浪费,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但是如果我们人类现在都知道这个地球最终是毁灭,我们又应该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信仰之外,要寻找意义,任何意义都不能够说服人,只有你自己能。
Q追问:你自己是什么在支持你?
谭伯牛:我就想尽量做一个诚实、正直、勇敢的人,还能够欣赏美。我觉得美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是时间中的人,我们偶然而生,突然而死,在中间混那么几十年,但是只有一个东西让我们超越时间,就是对美的欣赏,甚至创造美,甚至做美的好朋友。我觉得只有这个才能成为有超越性的一个东西。
Q5:请你推荐一下晚清的适合大众阅读的书。
谭伯牛:晚清的书很多了,《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日本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那一套,这些都可以。香港中文大学徐中约那个《中国近代史》,我觉得也很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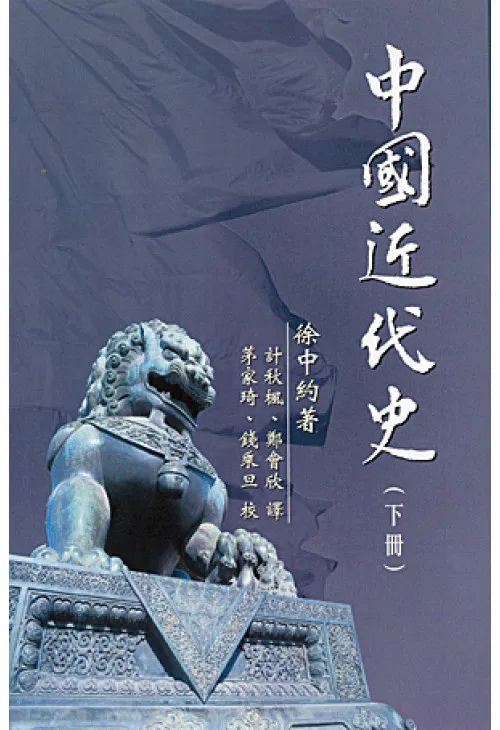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徐中约著
而且我觉得书是这样的,不能说我去开一个什么书单,我可以讲一讲大致的书单,或者开一个专题的书单。真正你要找书,你自己去找。书才会帮你找到书。我觉得读书就是开卷有益。
Q6:看历史总是三分悲哀,三分顿悟,三分感动,请问谭老师你面对历史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迷茫的感觉呢?
谭伯牛:我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讲初中开始看历史,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确实觉得我们近代史太屈辱了,受不了。有时候年轻人的情绪也比较饱满,看到中外太悬殊,甚至就感觉能落泪。但后来我也不仅仅看中国近代史,我们也要看看世界现代史,也要看看尤其是对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的理解。我有个新的变化,(自那以后)我就完全不再同情受到攻击和侮辱的中国近代的人。
我只讲一点,就是我对不平等条约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如果你一旦对这个不平等条约有一个客观的态度,你就不会觉得清朝那些皇帝、太后受到的打击,也会让你的心感到疼痛。
大家不要认为(鸦片战争的)赔款是胡乱来,人家是算出来的。第一,你打输了人家让你赔,这很正常。“打输住院,打赢坐牢”,这也是一个道理。第二点,签订了《南京条约》,接下来也有很多条约,我们叫不平等条约。既然要签订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如果我们两个人相安无事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用签订条约。那么这个里面当然不可能是五十对五十的,如果是五十对五十,我们不用签定这个东西。所以条约就是条约,没有不平等的条约。
还有第二个问题,条约签订了,哪怕一方觉得还是有些憋屈,那你要不要遵守?因为你签订这个条约的前提条件是你同意签,对方才停止殴打你,你不签,就会继续殴打你,所以你就已经签了之后,至少人家不打你了,你不还是占了一些便宜?所以你签了之后,你这还是应该执行、履行。
当然有一点,力量大了之后,条约就是废纸,铁血才是本质,这个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无法一定毁灭对方的情况下,我们都有点力量的情况下,我们就签订一个条约,苟且几十年,回头谁的力量小了,谁的力量大了,再修改条约或者取消条约,再说。你既然签了,最近这么几十年你还是应该遵守的。这个就是我对近代史不平等条约的看法的一个改变。
结语
薛野:谭老师,我们今天问了很多很多的角度,你来做一个小结。最后想和今天交流的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话?
谭伯牛:首先感谢大家的问题,那些问题都很有启发性。说实在的,我事先也没有准备要具体讲什么,尤其是跟薛野兄本来就是对谈,我也没有准备什么主题。有些问题其实我都没有太深入的思考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才启发我去思考,所以有些问题回应得应该也并不会太好。
另外有一点,历史也没什么标准答案,所以我的回答也不能做准。我只能讲我觉得未来我们是面临一个新时代、大时代。我们可以从乐观的层面讲,我们中国确实会见证历史,这不是一般人的幸运。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可能多多少少会对每个人的生活,对东西(方)都有很严重的影响,可能会是你前所未见的、从来没有想过的经历。所以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大家都多多保重。
薛野:谢谢主办方的安排,给我们一个对谈的机会,其实是学习的机会,能够从一个更大的尺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大历史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谢谢麓湖,也谢谢今天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今天以前我跟伯牛兄都是微信好友,今天我第一次认识,一下子起点就特别高。

活动现场

